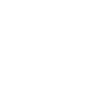以前看过一个社会新闻,很难忘。
有个男孩极聪明,家庭圆满,恋情美好,学业熠熠生辉。临近毕业去东南亚国家参与一个极重大项目,预计归国后就能跃升到很厉害的位置,然后结婚。
那边很热,男孩感染了疟疾,因为救治不及时,医疗条件也不太好,再回国内,男孩的大脑已经受到永久性的不可逆损伤。
这个损伤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他的双眼看不见了。
耳朵也再也听不到了。
其他一切正常。
记得当时有个作家也看到了这个新闻,认为这样的遭遇真的是无法言辞的极端的残忍。
我那时候设想了一下无声黑暗的世界,突然感到心跳出来胸口,人惊恐如溺水一般。
而他那么聪明,他曾经那么辉煌,他又怎么去接受呢?他的家人,又该如何面对他照顾他?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中有个病例,特别害怕孤独,她有句看起来是“疯言疯语”的对孤独状态的描述非常震撼我,她对作者也就是她的心理治疗师说,
当我孤独时,我就不存在。
这个男孩的孤独,是存在性的孤独,生理性的孤独,身体性的孤独,命运般的孤独。
他存在,可一切都不存在。
他不存在,可一切都还在。
多么伤人。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闻香识女人》里的弗兰克中校——或者上校?可能就能够有那么一星半点明白他没说出口的痛苦了吧。

弗兰克是老兵,战绩辉煌,曾是核心政要幕僚,能耐非凡,强横骄傲,风流倜傥。
但他在一次自己亲手造成的事故中双眼失眠,而他最好的战友——一个也非常著名的上校则因为他的失误而丧生。
弗兰克原本可以有光明的未来,有可以把后背交出去的战友,有他一生都在渴望的他醒来后依然在他身边的女人。
弗兰克也原本可以一直是家族的骄傲,是哥哥钟爱的弟弟,是姐姐尊崇的弟弟,是侄儿外甥女们的荣耀。
可是失明让他以为自己失去了一切。
弗兰克说,我是个烂人,一直都是。
独自一人住在不开灯的房间,弗兰克就只是不断地喝酒骂脏话打电话假装自己还是上校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
外甥女的小孩悄悄靠近他的窗户,他能精准地嘭一声扔枕头过去吓跑对方,猫咪想进到他的房间也会被他咆哮着吼出去。
外甥女和自己丈夫要出门一趟给他找来照顾他的高三学生西门被他百倍羞辱。
总之,弗兰克用恶毒和难以被靠近作为活下去的防护盾暂时活着。

弗兰克不知道自己有多厉害,可以鼻子轻轻一嗅,就能闻出任何一个女人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香水,哪怕没有香水用的是香皂也逃不过他的鼻子,可以几句话就让一个不被允许跳探戈也不会跳探戈的女孩和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跳一曲掌声雷动的探戈,还可以凭直觉开法拉利红色跑车一路飙车自行转弯……
弗兰克能欣赏西门的正直也能猜到乔治和乔治父亲如何行事,他在哥哥家受辱受嘲讽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西门,他警告对方无效后可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精准扣住对方喉咙,还能转身整理一下领结开开玩笑活跃气氛得体离开。
这样复杂到一言难尽也优秀到一言难尽的弗兰克,却想用枪将自己的脑袋射成稀巴烂。
带着西门去到纽约,为的就是践行这一计划。
当他不再恶毒不再雷厉风行不再让人感受到无尽压迫也不再胜券在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他一下子苍老疲惫绝望尽显。
西门说,是人都会犯错为什么就不能继续勇往直前呢?西门拼命夺过他手中的枪,对他说,他很优秀,很有魅力。
的确,在学校一番慷慨激昂脏话连篇的演讲,既救了西门,也让弗兰克收获一名漂亮女教授的主动靠近。
是的,后来弗兰克打算继续活下去了。
经历黑暗,痛苦,自我折磨和折磨他人,怀疑,审判,风光无限与深渊万丈后,弗兰克回到外甥女家,和她的女儿握手求和。
真希望那个男孩也是啊。